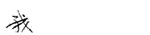梅山文化是至今仍集中保存于湖南中部、西南部的一种古老的原始渔猎文化,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界说似乎已基本认同。但从已有的研究论著来看,对梅山文化原始特性的理性分析却尚未展开。本文试从梅山文化的原始数理思维入手,探讨梅山文化的本质特征,解构“梅山”、“张五郎”等梅山文化重要文字(语言)符号的真实内涵,以此来认识梅山文化在湖湘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生成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珍贵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我认为,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梅山文化应解决的一个关键性课题。
一、梅山原始巫术中的“三”崇拜与中国古代数理文化“三生万物”的源流关系
“数”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原初思维工具,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莫不如此。中国初民的“结绳记事”,与后来发展形成的易卦数码推演系统,以及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阐释的“数是宇宙的本原,自然界是受数字支配的”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人类在认识“数”、掌握“数”这个工具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迷茫的原始数觉(“Number Sence”)时期。何谓原始数觉呢?原始数觉是人类童年时期对“数”的一种朦胧意识,即觉察数之有无与数之多少的感知能力。它犹如“味觉”、“嗅觉”、“触觉”一样,是人的一种本能感觉。
作为一种本能感觉,原始数觉并非人所专有。美国数学家丹齐克研究认为,人和动物都具有某种原始数觉。如,在有些鸟类的巢中如果有四个卵,那么你可以放心地拿走一个,鸟不会觉察;但如果拿掉两个,这鸟通常就会逃走。乌鸦也有某种原始数觉,它能辨别“四”位以下的人数。人类童年时期的数觉范围与某些鸟类一样,也是极为有限的,很少能达到“四”。“所以,在人类文明诞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三’往往也就成了与原始数觉相应的极限数,并且,因其极限性数位关系历史地常被人们用以表示‘多’的意义。”①许多语言几乎都带有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如英文的thrice和拉丁文的ter,都同样具有双重意义:“三倍”和“许多”。
在中国文化中,也能找到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如,用“三”座山来指代“很多的山”,用“三”棵树来指代“很多的树”,用“三”根火苗来指代“很多的火苗”,用“三”个人来指代“很多的人”——这就创造出了“山”、“森”、“火”、“众”等汉字(在甲骨文中,“山”是“三座山峰”的象形;“森”是“三棵树”的象形;“火”是“三根火苗”的象形;“众”字下边是“三个人”)。在古汉语中,还直接以“三”(以及三个“三”即“九”)来表示“多”。
这种状况反映在中国古代数理思维的集大成之作——《易经》中,就是阴阳两爻的合数和易卦的“单卦”、“重卦”编码都受“三”的制约:首先,易卦的“阳爻”和“阴爻”相加之和为“三”;其次,易卦的八个“单卦”均由“三”根爻叠加而成;再次,易卦的六十四个“重卦”亦均由两个“三”即两个“单卦”进行不同的叠加排列而成。
毫无疑义,在中国初民的原始数理思维发展过程中,曾存在一个无法超越“三”、对“三”充满迷惑、恐惧和敬畏的原始数觉时期。通过对梅山文化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我们惊讶地重睹了那个时期。
梅山文化作为一种原始渔猎文化,浸透了原始巫术的因子。古代的梅山人和今天的梅山巫术承传者们,在进山狩猎前要举行“安梅山”的原始巫术仪式。所谓“安梅山”,即给“梅山神”设坛并举行祭祀。安“梅山”要用“三”块石头或“三”块瓦片架在猪、牛踏不到的僻静地方,或安在“三”岔路口的古树下,表示梅山神在此;土家人安梅山大都选在屋角右侧空坪中的隐蔽洁净处,用岩石砌“三”面墙,上盖一块岩板,前面空着为门;猎人到了山上,如果发现野兽脚迹,要扯“三”根茅草,把草尖挽个疙瘩,放到“三”岔路口,拿块小石压上,这叫“封山(封三?)”;还有的猎人进山之后,随手折一根树枝,向这个山扫一下,向那个山扫一下,再绕自己所在的山头扫个圈(三座山),然后盘腿而坐,口念咒语,名为“下法”。——传说这样做了,野兽就会“迷”路,总是在山里转来转去,不会逃走。②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了梅山巫术的原初仪式对“三”这个数字的广泛运用,更注意到了这个仪式对“三”的运用是将其作为一种神秘力量来“迷惑”野兽!这与古汉语中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诸多中国民间宗教仪式及道教、佛教中对“三”这个数字的用法是不一样的——虽然它们在无意识中也是源于人类在数觉阶段所形成的“三”的心理积淀,但梅山巫术的用法更为古老,是对原始数觉“极限数”——“三”的“迷惑”特性的直接运用,属于一种更典型的原始数觉的“原生态遗存”。
梅山巫术中这种用“三”来“迷惑”动物的原始数觉特性,是梅山文化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特征除了在上峒梅山的山林狩猎活动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外,在中、下二峒梅山的水域平原农耕渔牧活动中也有反映。如,具有梅山神力的中峒“活梅山”在放鸭时,要用一根竹尖鸭梢“朝天划三个弧圈,再向前摇晃三下”,据说这样做了,鸭群就会朝着他指定的地点而去;而且到那里后,只“在鸭梢圈定的几块十几块田里的附近范围活动,从不越雷池半步”。下峒梅山巫术活动中“三”的运用要隐晦些。下峒“活梅山”在水田或水塘捉泥鳅时,首先要把捉到的第一条泥鳅的尾巴用口咬断,然后放回水里,据说这样做了,在捉泥鳅时泥鳅就会随手而来;但等到再捉到那条被咬断尾巴的泥鳅时,却不管这时捉到了多少泥鳅,整个捉泥鳅的活动就必须结束。③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举动呢?我认为这也是运用“三”来迷惑捕捉对象的一种巫术行为。这个过程很像易经阴阳二爻的形成和单卦的排序过程:第一条泥鳅表示阳爻“—”,把它咬断则裂变为阴爻“——”,这就恰好构成了一个数字“三”,把它放回水里,就是用“三”去迷惑对象;而再捉到那条泥鳅,表示复得阳爻,即一个单卦(“离卦”)的排序过程结束,所以必须停止捕捉泥鳅的活动。
梅山先民在原始数觉时期形成的这种对“三”的“迷惑”,不仅成为“三峒梅山”巫术的基本构架,更被作为一种神秘力量继承和定格在了梅山神张五郎身上。——在梅山文化中,张五郎就是一个具有“迷惑”法术特征的“倒路鬼”!梅山地区都这样传说:某人走夜路,如果在非常熟悉的地方迷失方向,转来转去又转到原处,怎么也走不出去,那他便是碰到了“倒路鬼张五郎”;因此,张五郎又叫做“倒路张五郎”。
在梅山地区,特别是梅山腹地的安化(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前现今涟源市和新化县的的一部分,古县城一直在现今安化县的梅城镇)、新化等地,人们往往还要在“三”岔路口立一块指路碑,上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八个字。一般传说这是为了挡“将军箭”,但“将军箭”与三岔路口毫无关联,因此我认为这最初也应当是用来防“倒路张五郎”的:在下峒梅山,张五郎又称“坛主”,据说他常常用箭射人(梅山人骂人常说:“你这坛主射的!”)。人们在三岔路口的指路碑上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八字,便是想以此作为咒语来挫败张五郎的法力,不让他的“迷惑”之箭射中,从而在三岔路口不迷失方向、走错路。
梅山巫术原初仪式中这种用“三”去迷惑渔猎对象的巫术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原始思维互渗律的体现。所谓原始思维互渗律,是一种决定原始社会集体关于它自身和它周围的人类群体与动物群体关系的思维规律。布留尔说:在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都具有一种可被感觉到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和作用,并且,这种神秘的属性可以通过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行动,通过接触、传染、转移、远距离作用、亵渎、占据、感应等想象的形式,作用于其它客体、存在物、现象;从而使原来的那些客体、存在物、现象同时既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事物就是通过原始人想象的“互渗”关系彼此关联起来的,在其反映形式上,某种集体表象也就与其他的集体表象彼此相互关联。④
梅山巫术对“三”的运用,正是企图通过这样一种想象的原始思维互渗关系,把“三”的神秘力量传递给动物。在梅山原始人类眼里,动物和人是同一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他们以为:“三”这个数字既然能迷惑人,肯定也能迷惑动物,从而他们在巫术中频繁地使用“三”,用“三”这个迷惑着人类自身的数字去迷惑野兽,以达到猎取野兽的目的。
梅山初民的这种原始思维互渗观念,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梅山文化作为一种原始渔猎文化,从经济形态看,整个狩猎分配过程具有鲜明的原始共产主义色彩;从原始宗教崇拜看,很多原始宗教礼仪保留着明显的原始生殖崇拜内容,因此,在其巫术活动中出现原始思维互渗观念,是很自然的。
至此,就梅山文化的本质意义而言,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原初的梅山文化,是一种以原始数觉极限数——“三”为媒介,借助“三”的“迷惑”力量,通过想像的原始思维互渗关系迷惑对象来开展渔猎活动的原始巫文化。她应产生于中国原始人类的“数觉时期”,是形成中国哲学“一生而,二生三,三生万物”观念的文化源头。而所谓“梅山”,其真实含义应为“媒三”(梅山腹地新化方言“山”即读为“三”);所谓“梅山文化”,其实也就是“媒三文化”。——“梅山”,当为后来的梅山文化圈以外的儒生们记音之误。